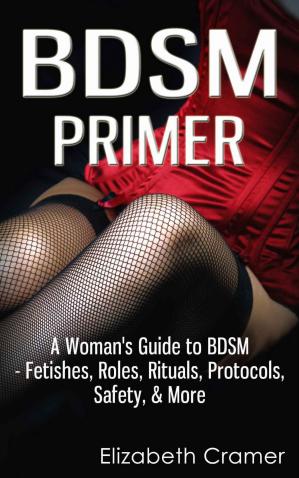学绳至今,也已个把个月。 回想最初见到绳缚,是在今年年初刚对BDSM稍感兴趣时,偶然买到的「花与蛇zero」影碟里。 那时整部片看完,只对里头把三人绑一块儿的绳缚表演场景印象深刻,但也不过是蔚为奇观,没作他想,直到后来在五月底的台大BDSM研讨会上听小林用「beautiful suffering」,描绘人经捆绑形成的姣好体态,因紧缚生成的隐忍神情,及沿着脖颈滑落的汗珠,才恍然领略此中惹我悸动的哀艳凄美,并立时为那样的画面心醉神迷。
为了亲手打造那样的画面,我开始学绳,尝试绳缚摄影,一心只想绑出别致的花样,拍出优美的作品。 尽管起初在MAYA的绳缚课上,我很快就学到绑缚的过程中应该要关照绳模的感受,无时无刻,花样百出,要查其所欲又要出其不意,以及拆绳重于绑缚等等道理,然而因那时我只把绳缚视作艺术,把绳模当成创作伙伴,所以在绑的过程中稍不留意,我就会陷入自个儿的创作情境里,全神贯注,与世隔绝,对绳模除了偶尔嘘寒问暖拉东扯西外, 就别无用心,从不仔细体察对方在这段受缚体验中真正想得到什么,只要最后能拍出合我心意的照片,我便沾沾自喜,觉得顺遂圆满。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实在自我得可怕。 被我绑过的绳模们当下没跟我计较,等到跟我混得更熟后才说,她们其实期待更认真的情欲经营。 可我虽依言作了修正,却也不过是顺应对方的要求而已,我仍然不敢主动探索对方的情欲,也不愿将自己的情欲与此产生连结。 就像和人结伙爬山,我一心只想攻顶,即使队友说了,这一路风景也很美的,我们一道看看嘛! 我虽答应了,也只是出自体贴的放缓脚步,好让队友方便欣赏,但自己仍是心系颠峰,直盯前方,无视美景,也无视队友想与我分享美景产生共鸣的心情。
于是这便在我和绳模之间构成一种古怪的隐微矛盾。 我贴近对方的身体,却远离对方的心; 对方把自己交给我,我却拒绝交出自己。 当然我也关怀对方,麻吗,累吗,渴吗,真心实意,但也仅止于此,我不试图作更深入的触碰,也牢牢封闭自己。 所以我可以逗趣,可以温柔,可以在嬉笑间营造浅薄的亲昵,但是一旦剥开这些,几乎再没有更深刻热烈的激情。
说是几乎,是因为让我发自内心因为绑人而亢奋的经验,其实还是有的。 除了面对爱人以外,有那么一次,几个朋友到我家彻夜吃酒闲聊,快天亮时,大家多少都醉了,即使是最清醒的我也有些茫。 那时其中一位曾说过她因为无法与人建立信任关系而不愿被绑的女孩,突然迷迷糊糊的对我说,要绑她就趁现在。 我起初还当她随口玩笑,直到她再次要求后,我才明白她的认真,一时兴起,便一口答应。
而那便是我至今绑过最酣畅淋漓的一次。 我不为拍照,不为练习,也与性无关,只专注的陶醉在绑的动作上,投入得就像随着音乐起舞,甚至仿佛因此唤醒蛰伏在我心底的什么,让我从中感到某种我不熟悉的放肆痛快。
事后回想,或许是因为酒精松动了我惯常的防备和节制,才造就这场对我来说有点魔幻的特殊体验,我既眷恋,又有点惧怕,毕竟那个被唤醒的什么正是我长久来所竭力驯养的,我目前还不愿再进一步释放它。 况且酒后绑人本就不太恰当,而若不靠酒,要进入那个状态对我来说要克服的障碍也实在太多,所以即使我嚐到甜头,也并未继续追求,依然故我,以为这样顶多就是不够好,不能动人,但也不至于造成什么伤害,反正社交不也是这么一回事吗? 这世道动辄挖心掏肺的人甚少,插科打诨,就图个彼此轻松愉快,也不算什么错事。
如此不久,我就咽到苦果。 随着学绳时间越久,我对自己要求越高,就越容易焦虑,只要绑得不美或吊缚不成,便情绪紧绷,意志消沉,失去和人调笑的余裕,放任气氛凝滞,此时我和绳模间的隔阂就会无从遮掩的益发明显起来,就像同床异梦一般无奈惨澹,让绳缚这件事瞬间失去意义,变得荒谬难堪。
那段时间我既自责又挫折,尤其当我在绳缚课上因屡次吊缚不成而对作我绳模的爱人动脾气后,无心再练,只好旁观起其他初学绳缚的学员,见他们即使只用简单的绑法都能和初次见面的人玩得开开心心,不禁难过的想,我到底在搞什么? 为什么我学了这么多,却反而连跟爱人都玩僵了呢?
然后我才发现,这除了与我在近距离接触下更容易暴露出来的各种根深柢固的性格缺陷有关外,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玩绳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放错了。 我为了摄影,要求画面,因此只要绑得不美或吊缚不成,无法达成目的,这次绑缚对我而言就算失败。 然而说到底,我玩绳缚摄影既不为求名获利,那最终不也是为了寻开心而已? 所以其实绑得不美或吊缚不成,都不要紧。
只要我和绳模在过程中能乐在其中,就不算失败。 不,精确来说,唯有如此,才是成功。
回想最初,时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绳缚,我大都简单回答,因我觉得绳缚很美。 如今我渐渐明白,绳缚的美,不仅只在于成果,也在于过程,而且比起看得见的,更重要的,应是那些看不见的,比如我们彼此交托信任,表露欲望,建立联系。
共渡一段灵肉都紧紧依存的珍贵时光。